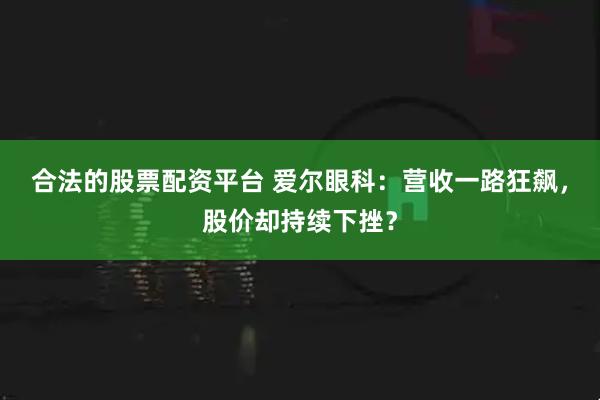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郑州股票配资公司
1940年,杨靖宇壮烈牺牲;4年后,他的妻子郭莲被投入粪坑惨死;
又过了8年,儿子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。
展开剩余92%村口照片没了人,马尚德也没了消息河南确山县一个村子,老百姓都叫马尚德“马大哥”,出门穿粗布中山装,干农活、打短工,时不时也跑些外地的事儿,别人问干嘛,他总说走亲戚。
他走得早,回来得晚,冬天也不闲着,人背厚毡,头上扣着棉帽,手里总拿根木棍,往地下一杵一杵,走得快得很。
老婆郭莲识字不多,整天围着两个孩子转。
她不爱说话,只管种菜、烧饭、看鸡舍,有人来家里敲门,她先把门闩紧再开口。
村里人说,她话少,脾气硬,男人不在也能把屋里屋外都撑起来。
那年春天,有人看见郭莲从屋里翻出一张照片,抹了半天,放进一个破布袋,又藏回地窖。
那地窖是放红薯和洋芋的,口小,能躲得住一只鸡。
这张照片,全家就这一张,照相馆盖了个戳,右下角用钢笔写了四个字:张贯一留,是个化名。
有人说那照片值钱,郭莲只回一句:你要也抹得动他胳膊,你拿去。
他走的时候,没说去干啥,村里传言有人见他出现在驻马店,又有人说他去了河北,后来没人再说得准,还有人提到“林区”,但谁也说不上是哪个林。
一个人影没了,两三年音信全无,只剩下一个名字被反复传来传去。
郭莲没吭声,大儿子马从云问爹去哪了,她也不多讲,只说你爹忙,有事。
那年冬天,村里换了保甲长,是个外来人,说话带外地腔,查户口查得紧,上门就盯着马家,问男人去哪了,是不是外出逃役,是不是搞联络。
郭莲照样只说:男人出远门,干苦力,走几年就回来了。
她眼神不乱,语气平,连手指都没抖。
几天后,两个陌生人出现在她家门口,穿的是便衣,腰上鼓鼓的。郭莲让孩子回屋,自己站在院子里迎着问话。
那天晚上,屋子被翻了,连炕席都掀起来,院子土被挖了三尺,照片差点被抢走。
她趁乱塞到灶台灰缸里,用柴火盖住。
半夜,她一个人蹲在灶门口,手里握着那张照片,头发披着,一句话不说。眼神像盯着灶缝深处,背影直得像块门板。
第二天早上,她照常下地喂猪,挑水,手臂青了大片,眼眶发黑,没人敢问一句。
被扔进粪坑淹死的时候,还在念丈夫的名字马尚德其实早已牺牲了。
1940年2月23日,吉林濛江县林海雪原,日军围住山沟口时,他带着少数部队转移。
他身中数弹,最后弹尽粮绝,咬破舌头,咽气时还坐在雪地里。解剖后发现胃里没有粮食,只有草根、树皮和棉絮。
日伪对尸体做了解剖处理。现场没有留下原名,也没人向河南通报。
一场埋骨雪地的牺牲,成了河南村里永远不清楚的谜。
郭莲不知道这些。她天天等,天天盯着门口。家里来过亲戚劝她改嫁,她把人赶出门。有人背地里说她倔,说她等的是鬼,她听到了,也没回一句。
白天砍柴,晚上哄孩子,夜里坐炕头,耳朵贴着门,听动静。她认定他会回来。
1944年,确山地区日伪联防司令部开始抓所谓“联络人”。有人指认马尚德曾是“张贯一”,可能和八路军有联系,郭莲家再被盯上。
两人直接上门提审。她没哭没吼,只说一口咬定马尚德是走西安讨饭去了,谁都联系不上。
那人冷笑一声说:讨饭的照片谁挂家里?
又是一通翻屋,炕沿被撬,米缸被倒。照片还是没找到。
她提前藏好了,塞进井口石板缝里,用灰浆糊住。她知道这个家到最后,什么都能扔,就那张照片不能没。
几天后她被抓走。
两天两夜不吃不喝,耳朵流血,嘴角裂开,眼睛肿得睁不开。那些人让她说出“张贯一”的真实身份。她嘴角动了动,还是没出声。
第三天下午,有人看见她被拖到村头粪坑边。
那个坑平常喂猪浇地用,味道冲得人发晕。
两人拽着她胳膊往下按时,她挣了几下,最后一头栽进去,连叫声都没有,路边有人吓得躲进草堆,有人看傻了,动都没动。
她就这么死了,被淹在粪坑里,连尸体都没人敢捞。
粪水盖过她头时,嘴里还在动,后来才有人悄悄说,最后一刻听她嘴里嘟囔一句:“你们父亲叫马尚德……”
那年,她四十岁。
儿子才七岁,女儿五岁,照片仍旧藏在井台底下的石缝里。
8年后,儿子在报纸上认出父亲照片马从云小时候记得,家里只有一张照片,母亲拿过来让他看过几次,一张泛黄相纸,上面一个男人站得笔直,眼神正、嘴角抿得紧。
他不懂,只记住那人叫马尚德。
母亲死后,家散了,亲戚把他和妹妹带出去,在外地躲了几年,那张照片一直贴在布衫里,夏天汗浸湿,冬天翻出来晾一晾。
每次摸到相纸边角,他就觉得心里揪着疼。
1949年,战争结束。他们回到了确山老家,屋塌了一半,地里长草。
有人来看过他们,是县里派来的,说要找革命烈士家属。
那时候没人知道他们父亲是谁,登记表格上空了一栏。那位干部摇了摇头,走了。
他把照片拿出来递上去,那人接过来看了几秒,说这人像东北那边的一个将军。
1951年7月的一天,他去镇上的供销社换粮票,门口摊着一份《河南日报》。
他随手翻了一页,一张照片猛地跳进眼里——熟得不能再熟,那是他记了十几年的脸。
图下写着: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。
他愣住了,眼圈一下红了。照片对比着他怀里的那张,一模一样,连站姿都没差。
他连夜赶去县里,一路抖着把照片递上去。
县里的工作人员看了又看,调出了组织资料,又找来回忆录一对,确认了。
马尚德,就是杨靖宇。
那一刻,他才知道,母亲守了一辈子、死前紧紧咬着的那个名字,和整本历史书上写的烈士是一个人。
更惊的是,那年他才十五岁,早就习惯被人叫“逃兵子孙”“穷小子”,没人提过“杨靖宇”这仨字。
消息一出,河南、吉林两地联动,很快成立家属认定小组,把他和妹妹送到北京做笔录,确认身份。
他看着工作人员翻那本烈士名册,翻到第128页停住,说:你父亲死得特别惨,尸体里一粒粮食都没有,肚子全是棉絮、树皮、草根。
他一句话也没说,坐在凳子上,腿一动不动,像被钉住了一样。
杨靖宇的名字立碑,马家三代走出村口1979年,马从云收到一封信,说吉林靖宇县要办纪念活动,邀请亲属出席。他把那张相片重新裱了框,坐火车去了东北。
靖宇县是以杨靖宇的名字命名的。他下车那一刻,站在站台上愣了很久。
周围都是穿军装的人,一张张烈士画报贴在候车大厅,有人念他的名字,报上来宾身份时,说了一句:“杨靖宇烈士之子。”
那一刻,他头一回抬起头走进会场。
整个礼堂很静,台上放着大幅遗照,他走进去时,有人起身鼓掌,他没说话,只点头,照片举在怀里,脸上像冻住一样。
座位上留着名字牌,他低头看到三个字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组织安排他进了铁路系统,工作安稳,日子也渐渐有了模样。妹妹在北京工作,后来也把那张照片复印了一张,挂在单位走廊。
那时候还没什么家庭照,别人问起来,她只说:“这是我爹,照片从我娘手里藏出来的。”
他走到哪,照片就带到哪。那照片成了他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。
杨靖宇的墓碑,建在吉林靖宇县。最早的一块,是松树刻的简碑,写着:“抗联司令杨靖宇长眠于此”。
后来换了石碑,再后又刻上照片和生卒年。
墓旁种了三棵松树,站成三角,一棵面北,两棵斜斜向南。
2000年初,马从云的儿子也站在墓前,看着爷爷的名字,说了一句:“我们一家三代,全靠这个名字活下来了。”
他没说谎。
那个名字,一度失踪、沉没、被埋,直到十几年后才被重新喊出来。
就像那张照片,从泥灰缝里被抠出来,从报纸上翻出来,从烈士名册里对出来。
——四口之家,只剩两人活到确认那天。
一个死在白雪郑州股票配资公司,一个死在粪坑,一个没见到墓碑,一个直到1951年才知道,自己是杨靖宇的儿子。
参考资料: 民闻网历史栏目:《杨靖宇牺牲后,郭莲之死全村无声,儿子如何得知真相?》发布于:河南省极速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